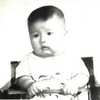 一丁,肉吃多了,未能远谋
一丁,肉吃多了,未能远谋
谢谢 @知识库 邀请~
如有错误,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亚圣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倒不是说孟子就开始支持安乐死,而是说明古人对于死的态度起码与“安乐”有所联系。曾子也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可谓孝矣。”自古以来,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对待亲人的死亡更为“事重”,这也使得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变得极为有意义。而我们对死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一、关于安乐死,我国法律是怎么规制的?
在我国法律上的安乐死,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在其《犯罪通论》中将安乐死定义为:所谓安乐死,又称安死术,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无法治疗,且濒临死亡,为了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基于患者本人的请求或者同意,采用适当的方法,促使其提早死亡的行为。
而在学理上也会把其分为“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
所谓积极安乐死是指医生在为重病患者解除痛苦时采取积极的作为方式,比如注射致死药剂等,使病患快速死亡;所谓消极安乐死则是指医生在治疗重病患者时,为消除其痛苦而采用消极的不作为方式,通过停止使用维持病人生命的医疗措施等方式,使之死亡的行为。
“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区别在于是否有病患自我同意)等类别。
但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安乐死”并没有实际上的“合法化”,也是不被官方所承认的。例如在司法行政系统作成的相关文件中是这样写的:
关于不宜办理“安乐死”公证事项的复函
安徽省司法厅公证管理处:
你处皖司公(1989)018号《公证机关能否办理“安乐死”公证证明的请示报告》收悉。关于能否为病人的“安乐死请求书”办理公证证明,经商有关部门认为,我国对“安乐死”尚无法律规定。所以公证机关不宜办理无法律依据的“安乐死”方面的公证事项。
1、那么如果真的有人实施了安乐死怎么办?
在刑法上,因为不认为安乐死的“合法”,实行者与辅助实行者(亦即所有类别的安乐死)的行为与死者都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且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并没有承诺能力。因而,都会被判定为“故意杀人罪”,但在实际司法活动会根据情节、前后实际情况予以法定刑以下的刑罚。
例如之前被报道过的“拔管杀妻案”,“孝子杀母案”(以链接中所述的)最终都被处以缓刑,而未被判处实刑。现今随着裁判文书的公开,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版本的“安乐死杀人案”:
例如在(2015)武刑初字第10号 “被告人冯刚犯故意杀人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冯刚受死者本人要求给瘫痪在家难耐之祖辈刘爱美服用过量安眠药最后致死。对于最后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的判决,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是这样写到的:
本院认为,被告人冯刚对于他人要求自杀的行为提供帮助,且在自杀行为施行后未履行抢救义
务,其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武城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控成立。
同时,被告人冯刚的行为基于其家庭生活特别困难、被害人非常痛苦且无有效治疗手段等前提
下,其主要目的是帮助被害人完成解脱痛苦,其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都较他种杀人行为明显为轻。
根据刑法理论,被害人的同意是阻却或减少可归责性的重要事由。
但我国普遍伦理、社会舆论与立法实践,尚不认可安乐死行为的合法性。
故被告人行为仍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责任。
被告人冯刚对被害人的死亡持放任态度,是间接故意杀人,属于故意杀人中情节较轻的情况。
被告人与被害人系祖孙关系,其故意杀人的行为系应被害人的主动要求,社会危害性较小,被
害人其他家属对被告人冯刚表示谅解,并请求法院对冯刚从轻处罚,被告人冯刚认罪态度较好,可
酌情从轻处罚。
处其缓刑不会对社区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可依法适用缓刑。
“管中窥豹”,刑法原则强调“罪刑法定”,而这样的处置,也可以略见司法实践中并不照搬法律规定,而有了灵活的处置。
但在此还是要说明,在我国大陆地区,无论是被承诺的还是自我实行的“安乐死”都有极高的“法律风险”,虽然“爱之深”,但依然是触犯了强制性法律规定。
2、我国大陆地区会否实行安乐死合法化?
这个问题如同“我国是否废除死刑?”一样,能用一个句式来回答:“学术界与医界大多都认为安乐死是一个趋势,但这并不是现在我们马上要做的。”
除去现实的我国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客观条件,目前我们看到的安乐死基本是由近亲属所实行的,这同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并且如何防止安乐死被滥用,在条件上如何设立,这也是立法上需要严格考虑的问题。
而从“科学伦理”而言,也依然会出现很多人不支持,即便说现在随着人文关怀的普及,大家对于生命的尊重也逐渐扩大到了对“安乐死”的支持,但无法忽视的是依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民群众是根本无法接受“安乐死”的。就如同上述所引案例中
不过毫无疑问,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医学知识的普及,临终关怀的被重视,我个人相信对于安乐死合法化的操作也是会提上日程的。
二、关于安乐死,其他法域的进程是怎样的?
迄今为止,也只有少部分的国家与地区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合法化的安乐死”,诸如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案的荷兰可以说是较好的“典范立法”。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通过一些关于安乐死的判例,逐渐使得社会大众能够接受“消极的安乐死”,虽然并不对“积极安乐死”持支持态度,但同样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犯罪问题。并且还提出了对于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六个可能条件:
(1)根据当时的医学知识和技术条件,患者患的疾病是不可治愈的并且临近死亡期限非常临近;
(2)病人的疼痛和痛苦是无法忍受的,病人的痛苦让人不堪目睹,而且这结论要由专门的观察人员作出;
(3)安乐死的唯一目的必须是为了减轻患者的疼痛和痛苦;
(4)患者自己要求或同意实施安乐死,而且这种要求和同意必须是患者在清醒的状态下并且能够充分表达自己意思的情形下做出的;
(5)原则上,安乐死必须由医生来实施,必须有特殊的可信理由证明为什么没有由主治医师实施安乐死;
(6)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在道德上必须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说截止到今天为止,日本也并没有真正完成“安乐死除罪化”,但这股思潮和荷兰通过安乐死法案一样,确确实实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包括最近被报道的傅达仁先生在内的民众推动下,早于2016年就已经公布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与之配套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实施细则》在2019年1月6日正式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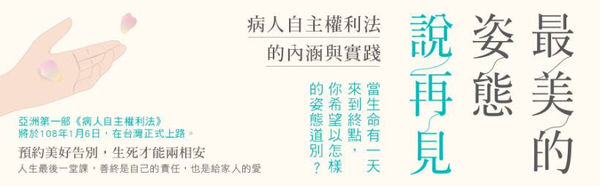
根据相关条款,在病症末期、不可逆转的昏迷、永久植物人、极重度失智、痛苦难忍或无法治愈这五种临床条件符合其一,成年国民便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通过一定的程序预先确立自己今后要在此种情况下如何离开这个世界,包括但不限于选择接受何种医疗方式。据此,只要得到了病人亲友“允诺”,那么就不会出现之前所谓的“遗嘱杀人”情况。这在很大意义上已经为“安乐死除罪化”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也使得我国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传统的生死观、儒家思想的孝道使得安乐死在中华民族的实施之路带来了的现实困境有了“检验之处”。
也让我们期待更好的明天~